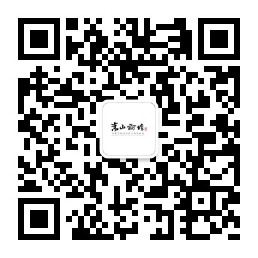中华“和合”文化的内涵探讨
日期:11-26
李龙海
中原工学院
摘要“和合”220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积极成果,是华夏民族特有的哲学词汇和价值观念,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和终极价值。
“和合”二字并举,首见于《国语·郑语》所载的“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由此形成“和合”的概念及范畴。和合的“和”是和谐、和平、和睦、中和、祥和、和善,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是结合、融合、合作,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和”、“合”连用,突出强调事物是不同因素的相异相成。基于“和合”文化在典籍中所表达的含义,笔者把中华和合文化的涵义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Examining the Meaning of ‘Harmony’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LI Longhai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I Longhai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hehe (‘harmony’) is central to unlocking the inner laye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has remained an elusive ideal for generations of Chinese artists and thinkers. The two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combine to make up hehe (和合) are complementary rather than
220 “和合”有时也可写成“合和”,其涵义是一致的。如《吕氏春秋》“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史记·五帝本纪》说尧“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汉书·杜延年传》的“合和朝廷”; 《史记·乐书》的“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后汉书·杜诗传》的“海内合和,万姓蒙福,天下幸甚”等等。
identical: the first represents “pacification”, while the second stresses “integration”. We examine references to hehe in a series of classical texts with a view to deepening awareness of the various nuances of the contemporary term.
The concept of hehe (‘harmony’) is central to unlocking the inner laye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has remained an elusive ideal for generations of Chinese artists and thinkers. The two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combine to make up hehe (和合) are complementary rather than
220 “和合”有时也可写成“合和”,其涵义是一致的。如《吕氏春秋》“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史记·五帝本纪》说尧“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汉书·杜延年传》的“合和朝廷”; 《史记·乐书》的“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后汉书·杜诗传》的“海内合和,万姓蒙福,天下幸甚”等等。
identical: the first represents “pacification”, while the second stresses “integration”. We examine references to hehe in a series of classical texts with a view to deepening awareness of the various nuances of the contemporary term.
一、 确认事物间以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前提的包容性
多元共存是和合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包容性又以承认事物间存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前提。“和”蕴涵着“他”与“他”的关系,即互相差分、对待、冲突的事物,互相融合或平衡;阴阳和而万物生,或金木水火土差分、冲突合而成百物。《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韦昭注:“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意思是说商契能把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国语·郑语》还记述了史伯关于“和、同”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禅同,尽乃弃矣。”史伯认为 “和”是不同元素的结合,不同、差别是“和”的前提,这样的“和”才能长久,“和成”的物才能丰长。如果“去和取同”,那就会“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以此治国,就会排斥异己、独断专行,这就离灭亡不远了。史伯由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和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作用中认识到“一”与“多”的辩证关系,换言之,即事物的统一体是由多种不同事物或多种不同因素综合而成的。春秋时,晏婴进一步发展了史伯的这一思想,《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齐侯与晏子论“和”的故事221。“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酰、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1](昭公二十年) 晏婴把和、同之异作了非常生动而深刻的比喻,指出“和合”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矛盾多样性的统一,强调不同品质的物质协调配合才能产生新的效应,生成宇宙万物。
221 又见于《晏子春秋·外篇第七》。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是万物之母,“天地感而万物化生”[2](彖传)。《象传·泰》曰“天地交,泰”;《象传·否》载“天地不交,否”。这段话旨在说明,天地只有相交,才能达到和谐;反之,天地不相交,则无法达到和谐。老子也提到“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3](第四十二章)。老子又讲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指出了万物的和合相生规律。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4](子路),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理想境界。意即个性行为虽有区别,但道德修养好的人能以自己的思想协调各种矛盾,使一切事情做到恰到好处,处于和谐状态,而不盲从附和。道德修养差的人却一味盲目苟同,人云亦云,而不善于协调,从而难以达到真正和谐。孔子的这种思想所体现的是传统文化中对和谐的另一种认识和把握,即强调主体间及主客体间相互协调、配合得当促进主体和事物的发展,同时也要保持主体的个性和事物自身特色,以利于主体和事物在和谐的联系中按自身规律持续发展。冯友兰先生曾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他还拿饮食与音乐作比方,“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各种味道,不同声音,配合起来,那是‘和’”。[5] 张立文先生也指出“和合是诸多异质因素、要素的冲突融合,即多元和合。和合首先需要承认多元的、多样的事物的存在,它不是一元的,一元即是同、单一、唯一,‘同则不继’。”[6](P429)
和合思想的核心是和,既承认事物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同时也不是排斥基于事物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而带来的事物间的矛盾和斗争。和合思想鼓励人们用适当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冲突和斗争,把事物的矛盾、冲突和斗争限定在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防止因过度的矛盾斗争而破坏了不同事物共同存在的基础。因此,和合思想在选择解决矛盾的方式方法时,不是要激化和扩大矛盾,而是尽最大努力弱化这些矛盾的强度,通过寻找和扩大共同点,取得有利于矛盾各方的最佳结果。《乐记·乐礼》:“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孔子也说:“天地不合,万物不生”[4](哀公问)。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的思想中就有极为可贵的和合思想。荀子通过对天地自然、人伦社会的深入探究,深刻地认识到“和合”乃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事实上,只有在承认不同事物的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不同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且不断地取长补短,使不同事物之间达到最佳组合,才能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因此,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7](天论),“天地合而万物生”[7](礼论)。张立文先生即指出:“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不同文明间诸多形相和无形相互相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的过程中各形相和无形相和合的新生命、新事物、新结构的总和。”[8] “冲突的关键点亦越明显;和合的下手处亦愈明确。”[6](P89)
221 又见于《晏子春秋·外篇第七》。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是万物之母,“天地感而万物化生”[2](彖传)。《象传·泰》曰“天地交,泰”;《象传·否》载“天地不交,否”。这段话旨在说明,天地只有相交,才能达到和谐;反之,天地不相交,则无法达到和谐。老子也提到“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3](第四十二章)。老子又讲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指出了万物的和合相生规律。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4](子路),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理想境界。意即个性行为虽有区别,但道德修养好的人能以自己的思想协调各种矛盾,使一切事情做到恰到好处,处于和谐状态,而不盲从附和。道德修养差的人却一味盲目苟同,人云亦云,而不善于协调,从而难以达到真正和谐。孔子的这种思想所体现的是传统文化中对和谐的另一种认识和把握,即强调主体间及主客体间相互协调、配合得当促进主体和事物的发展,同时也要保持主体的个性和事物自身特色,以利于主体和事物在和谐的联系中按自身规律持续发展。冯友兰先生曾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他还拿饮食与音乐作比方,“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各种味道,不同声音,配合起来,那是‘和’”。[5] 张立文先生也指出“和合是诸多异质因素、要素的冲突融合,即多元和合。和合首先需要承认多元的、多样的事物的存在,它不是一元的,一元即是同、单一、唯一,‘同则不继’。”[6](P429)
和合思想的核心是和,既承认事物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同时也不是排斥基于事物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而带来的事物间的矛盾和斗争。和合思想鼓励人们用适当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冲突和斗争,把事物的矛盾、冲突和斗争限定在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防止因过度的矛盾斗争而破坏了不同事物共同存在的基础。因此,和合思想在选择解决矛盾的方式方法时,不是要激化和扩大矛盾,而是尽最大努力弱化这些矛盾的强度,通过寻找和扩大共同点,取得有利于矛盾各方的最佳结果。《乐记·乐礼》:“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孔子也说:“天地不合,万物不生”[4](哀公问)。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的思想中就有极为可贵的和合思想。荀子通过对天地自然、人伦社会的深入探究,深刻地认识到“和合”乃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事实上,只有在承认不同事物的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不同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且不断地取长补短,使不同事物之间达到最佳组合,才能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因此,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7](天论),“天地合而万物生”[7](礼论)。张立文先生即指出:“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不同文明间诸多形相和无形相互相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的过程中各形相和无形相和合的新生命、新事物、新结构的总和。”[8] “冲突的关键点亦越明显;和合的下手处亦愈明确。”[6](P89)
二、 强调事物间的差序性和主导性
在和合思想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事物间的尊卑有序。《易·系辞传》论述宇宙生成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就其性质来说,称阴阳;就其法象来说,称天地;就《周易》的语言来说,称乾坤。《易传》的和合思想就是从阴阳的对立统一入手而展开的。太极为宇宙万物之本源,它的本源性正在于它的阴阳两性。但是,在《易传》中,阴阳两性的地位并不平等,而是阳主阴从,阳尊阴卑,阳大阴小。《易·系辞传上》开宗明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传》的干,就是阳,代表天、君、父、夫等刚健性事物;坤,就是阴,代表地、臣、子、妇等柔顺性事物。“天尊地卑”一句话,就确定了干、坤两类不同事物的尊卑地位。其尊卑序列的表现形式是《易》卦的六爻之位。故《系辞传上》说:“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韩注、孔疏说六爻之位贵贱在上下,“皆上贵而下贱也”。卦的大小在阴阳,若《泰》阳长阴消,曰“小往大来”;《否》阴长阳消,曰“大往小来”。《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这里儒家说的礼也是有等级的。周代的礼,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等级性都是很严格的,并且这种等级性的礼制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9](曲礼上) ,一语道出了对礼有使用权的主体阶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即统治阶级内部因爵秩等级不同,所享受的礼遇也有差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又说:“自上以下,隆杀以两。”杀即减。是说自上而下爵秩每减一级,相应的礼遇就削减二数。如《周礼·春官·典命》载,上公旗冕皆九旒,侯伯则七旒,子男五旒,即所谓“隆杀以两”。《礼记·中庸》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曲礼》曰:“夫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在周代社会中,“亲亲之杀”反映的就是血族关系的等级;“尊贤之等”反映的就是社会上的政治等级。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讲的就是以等级制为基础的礼,要恪守尊卑贵贱不同等级的和合。故张立文先生就此总结到:“万物高下有序,高下而有差分,差分而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行各业并育而不相害。”[10]
和合思想在强调事物间存在差序性的同时,又强调其间必有一事物其起主导作用。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上,以和合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始终立于主导地位。先秦时期,尽管百家争鸣、各展其说,但他们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的话题来探讨,那就是道,其宗旨是消除春秋战国频繁的战乱,给人民以安身立命之道。所以《周易》中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化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隋唐时期,佛教文化的盛行,一度使儒家文化有所淡薄。但到了宋明时期,以程颢、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进一步把中国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与佛教文化融合起来,建构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即宋明理学,也被称之为“新儒学”,一直延续到近代。
和合思想在强调事物间存在差序性的同时,又强调其间必有一事物其起主导作用。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上,以和合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始终立于主导地位。先秦时期,尽管百家争鸣、各展其说,但他们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的话题来探讨,那就是道,其宗旨是消除春秋战国频繁的战乱,给人民以安身立命之道。所以《周易》中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化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隋唐时期,佛教文化的盛行,一度使儒家文化有所淡薄。但到了宋明时期,以程颢、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进一步把中国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与佛教文化融合起来,建构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即宋明理学,也被称之为“新儒学”,一直延续到近代。
三、 追求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
“天人合一,和谐共生”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和谐共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人生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了“天人合一”观念源起与演变的基本过程,贯穿于古代的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中。
“天人合一,和谐共生”就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践行“因天”“因时”的理念。古代典籍中有诸多相关记载。如《周易·文言》即明确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顺应自然的“因天”“因时”的思想。《中庸》中记载孔子“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就是说孔子遵循时间,因地制宜,按照自然之“道”进行活动。《管子·侈靡》载:“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实,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和规律,《礼记·乐记》中亦有“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的记载。孟子在对梁惠王陈述兴邦大计时说:“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11](梁惠王上) “数罟”是细密的网子,“以时”即按适当的时间。《管子·宙合》载:“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阴,冬处阳”,这些都是“因时”的观念。《荀子·王制》也有“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的记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取之有度”的思想,另外墨家也提出节用、节葬的思想。这种天人合一,万物和谐共生的理念不但但是思想家的主张,而且还体现在国家的政府机构的设定与法律制度上面,据《周礼》所载,在周代专门设有 “野虞”“山虞”“泽虞”“水虞”“林衡”“川衡”等保护鸟兽、山林、湖泽及产物的官员。周、秦的国家法律都有定期封山,禁止伐木等保护自然的法律条文。甚至在民间也有“劝君不吃四月鱼,万千鱼仔在腹中;劝人不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谷雨前,好种棉;谷雨后,好种豆”的农谚。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第二十五章)
,认为宇宙间有四大,人居其一,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从一个侧面确立了人与天的相互关联。庄子提倡“与天为一”,《庄子·达生》云:“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抛弃世事,忘怀生命,使形体健全,精神饱满,从而达到与天合为一体的自然无为境界。
与思孟学派“物我不分”、“天人不二”的思想有所不同,荀子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7](天论) 的思想,即其天人关系中的和合思想是以“分”为前提的,由分”而和,由“分”而合,由分而“参”。“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7](天论)。在荀子看来,“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阴阳风雨、四时变化,都同属于物质世界,即所谓“万物同宇而异体”[7](富国)。“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7](天论)。荀子努力向人们证明,一向被当做神来崇拜的“天”其实质不过是没有人格、没有意志,按照自身规律不断运动变化着的自然。荀子的意图很明确,即在破除人的迷信和无知的同时,消除人的自卑,确立人的自信,凸显人的主体性,从而恢复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尊严,在更高层次上求达天人之间的和合统一。一方面,荀子认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
[7](天论),另一方面,荀子认为人在“天”的面前并非一个可怜的被动的存在,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在他看来,只要辨知天地万物之理而加以制用,那么人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就可以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便可以达到“天地官而万物役”、“与天地参”的和合境界。
钱穆先生在他的遗稿中曾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人”思想有过一个评价,他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注重和合,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特性。”[12] 由此可见,“天人合一”的理念最能体现中国文化本质,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与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
“天人合一,和谐共生”就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践行“因天”“因时”的理念。古代典籍中有诸多相关记载。如《周易·文言》即明确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顺应自然的“因天”“因时”的思想。《中庸》中记载孔子“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就是说孔子遵循时间,因地制宜,按照自然之“道”进行活动。《管子·侈靡》载:“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实,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和规律,《礼记·乐记》中亦有“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的记载。孟子在对梁惠王陈述兴邦大计时说:“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11](梁惠王上) “数罟”是细密的网子,“以时”即按适当的时间。《管子·宙合》载:“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阴,冬处阳”,这些都是“因时”的观念。《荀子·王制》也有“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的记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取之有度”的思想,另外墨家也提出节用、节葬的思想。这种天人合一,万物和谐共生的理念不但但是思想家的主张,而且还体现在国家的政府机构的设定与法律制度上面,据《周礼》所载,在周代专门设有 “野虞”“山虞”“泽虞”“水虞”“林衡”“川衡”等保护鸟兽、山林、湖泽及产物的官员。周、秦的国家法律都有定期封山,禁止伐木等保护自然的法律条文。甚至在民间也有“劝君不吃四月鱼,万千鱼仔在腹中;劝人不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谷雨前,好种棉;谷雨后,好种豆”的农谚。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第二十五章)
,认为宇宙间有四大,人居其一,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从一个侧面确立了人与天的相互关联。庄子提倡“与天为一”,《庄子·达生》云:“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抛弃世事,忘怀生命,使形体健全,精神饱满,从而达到与天合为一体的自然无为境界。
与思孟学派“物我不分”、“天人不二”的思想有所不同,荀子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7](天论) 的思想,即其天人关系中的和合思想是以“分”为前提的,由分”而和,由“分”而合,由分而“参”。“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7](天论)。在荀子看来,“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阴阳风雨、四时变化,都同属于物质世界,即所谓“万物同宇而异体”[7](富国)。“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7](天论)。荀子努力向人们证明,一向被当做神来崇拜的“天”其实质不过是没有人格、没有意志,按照自身规律不断运动变化着的自然。荀子的意图很明确,即在破除人的迷信和无知的同时,消除人的自卑,确立人的自信,凸显人的主体性,从而恢复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尊严,在更高层次上求达天人之间的和合统一。一方面,荀子认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
[7](天论),另一方面,荀子认为人在“天”的面前并非一个可怜的被动的存在,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在他看来,只要辨知天地万物之理而加以制用,那么人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就可以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便可以达到“天地官而万物役”、“与天地参”的和合境界。
钱穆先生在他的遗稿中曾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人”思想有过一个评价,他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注重和合,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特性。”[12] 由此可见,“天人合一”的理念最能体现中国文化本质,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与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
四、 中庸之道的处世哲学
“中”在哲学和思维方法上具有方法论的含义,朱熹曾对“中庸”有过解释:“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13](中庸章句) 可见,中庸的根本是适中。中庸之道是“和合文化”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具体准则,它在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作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追求目标。
西周时期,周人确立了“明德慎罚”的德治思想,并在具体的实践了形成了“尚中”的伦理观念。如《尚书·吕刑》中有“咸庶中正”、《酒诰》中有“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周易》里有“中吉”、 “师中”, “中行”、“中孚”等概念 ,都是一种肯定性的价值判断,充分体现了周人的尚中思想。同时,周人尚“中”的道德理念也落实到立法与司法领域之中,并形成了“中刑”(或“中罚”、“中正”)的立法与司法原则,反映了“慎刑”的法律价值取向。例如,上举《周易》中的《讼卦》卦辞云:“讼,有孚、窒、惕,中吉。”此所谓“中吉”就是说司法官要秉公执法、量刑适中,这样才能使断案吉祥。《尚
书·立政》云:“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这句话把“慎”与“中罚”结合起来,揭示了“中罚”原则所体现的慎刑精神。《尚书·吕刑》载:“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就是要求司法官根据刑书所载的条文谨慎地定罪量刑,使刑罚公正适中。西周铜器《牧簋》铭文也有 “不井(刑)不中”,意谓刑罚不适中就不要施行。可见,周人是把“中刑”作为重要的司法原则来推崇的。
周人把“中”作为基本的道德原则,这对后世儒家影响很大。孔子时,提出了“中庸”的概念,并把“中庸”视为最高的道德,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4](雍也) 中庸主张不偏不倚,执两用中,故“执两用中”为中庸的核心。孔子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了“中庸”思想,如他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卫灵公) 、“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4](雍也 )、“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4](尧曰) 的做人原则,将其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成了儒家崇尚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4](颜渊) 的理想追求。
后来,子思作《中庸》,对中庸之道又进行了系统详密的论证,并又明确把“中”与“和”融合起来,提出“德莫大于和”的思想。并对“中”与“和”的关系了分析,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由此,“中和”上升到了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升华为天地宇宙和社会人生运行的理想图式,而“中和”也就是和合。
和合文化自其形成之时,就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隽永的魅力,并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历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虽历经沧桑,却历久弥新。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和处理全球问题的智慧。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的建设。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大力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建设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新型政党制度。在文化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以及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在社会建设的目标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一词并成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与“美丽中国”的生态建设目标。在处理日益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和人类前景方面,中国政府提出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观等等。以上所列几项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和合”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当今中国在解决国内问题与全球问题时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西周时期,周人确立了“明德慎罚”的德治思想,并在具体的实践了形成了“尚中”的伦理观念。如《尚书·吕刑》中有“咸庶中正”、《酒诰》中有“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周易》里有“中吉”、 “师中”, “中行”、“中孚”等概念 ,都是一种肯定性的价值判断,充分体现了周人的尚中思想。同时,周人尚“中”的道德理念也落实到立法与司法领域之中,并形成了“中刑”(或“中罚”、“中正”)的立法与司法原则,反映了“慎刑”的法律价值取向。例如,上举《周易》中的《讼卦》卦辞云:“讼,有孚、窒、惕,中吉。”此所谓“中吉”就是说司法官要秉公执法、量刑适中,这样才能使断案吉祥。《尚
书·立政》云:“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这句话把“慎”与“中罚”结合起来,揭示了“中罚”原则所体现的慎刑精神。《尚书·吕刑》载:“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就是要求司法官根据刑书所载的条文谨慎地定罪量刑,使刑罚公正适中。西周铜器《牧簋》铭文也有 “不井(刑)不中”,意谓刑罚不适中就不要施行。可见,周人是把“中刑”作为重要的司法原则来推崇的。
周人把“中”作为基本的道德原则,这对后世儒家影响很大。孔子时,提出了“中庸”的概念,并把“中庸”视为最高的道德,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4](雍也) 中庸主张不偏不倚,执两用中,故“执两用中”为中庸的核心。孔子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了“中庸”思想,如他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卫灵公) 、“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4](雍也 )、“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4](尧曰) 的做人原则,将其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成了儒家崇尚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4](颜渊) 的理想追求。
后来,子思作《中庸》,对中庸之道又进行了系统详密的论证,并又明确把“中”与“和”融合起来,提出“德莫大于和”的思想。并对“中”与“和”的关系了分析,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由此,“中和”上升到了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升华为天地宇宙和社会人生运行的理想图式,而“中和”也就是和合。
和合文化自其形成之时,就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隽永的魅力,并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历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虽历经沧桑,却历久弥新。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和处理全球问题的智慧。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的建设。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大力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建设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新型政党制度。在文化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以及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在社会建设的目标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一词并成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与“美丽中国”的生态建设目标。在处理日益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和人类前景方面,中国政府提出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观等等。以上所列几项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和合”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当今中国在解决国内问题与全球问题时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 考 文 献
[1]左丘明.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易[M] . 北京:中华书局,1980.
[3]老子[M] . 北京:中华书局,1980.
[4]论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张立文.和合学――21 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7]荀子[M] . 北京:中华书局,1980.
[8]张立文.中华和合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J],社会科学研究,1997,(5).
[9]礼记[M] . 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张立文.弘扬传统和合思想 建构现代和谐社会[J],人民论坛,2005,(2).
[11]孟子[M] . 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J],中国文化,1991,(1).
[13]朱熹.四书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1]左丘明.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易[M] . 北京:中华书局,1980.
[3]老子[M] . 北京:中华书局,1980.
[4]论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张立文.和合学――21 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7]荀子[M] . 北京:中华书局,1980.
[8]张立文.中华和合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J],社会科学研究,1997,(5).
[9]礼记[M] . 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张立文.弘扬传统和合思想 建构现代和谐社会[J],人民论坛,2005,(2).
[11]孟子[M] . 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J],中国文化,1991,(1).
[13]朱熹.四书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